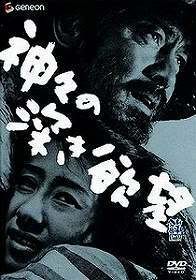之前erica提议我找一家茶座好好想想自己将来的打算,虽然还没有真正落实去准备,不过茶座倒是我在这个月的大半时间里面每日光顾的地方。
这个多月看过的书不是特别多,但也不算少,基本上跟我的movie adventure同步。看小津同时在看《东京物语》的论文集;看Bresson就找他的作品赏析;现在看Ingmar Bergman也自然而然地跟他的biography一起欣赏。深受家庭的宗教背景影响的Ingmar Bergman曾经怀疑过,点评他的作品的撰稿人如果连路德派的catechism都没有读过怎样去切入他的作品。而对如我这样的film buff而言,要专门去读教义来理解一个导演比较demanding,但从他的传记里面却可以很全面地看到一个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对他作品的众多影响。这方面Bergman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他童年经历的再现和放大。好像Shirlie提到他的《第七封印》明显体现Bergman对中世纪欧洲历史和社会的透彻研究和了解,稍稍了解Bergman的童年就发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Bergman出生和成长的Uppsala市就是北欧历史最悠久的古城,加上Bergman父亲的教士职业,他从出生开始就被众多教堂、城堡和学院所环抱,其中很多还是中世纪的古迹。《第七封印》里面反映死神将临和大瘟疫时期信众的自虐式游行的教堂壁画,就是Bergman从小看到大的。所以贯穿Bergman的一生,阅读和了解中世纪的北欧都是他的持续兴趣,与其说是为《第七封印》而做这些research,不如说是因为对这个时期的浓厚兴趣而产生《第七封印》这部力作。而Bergman的童年竟然以看园丁搬运死尸和看医院焚化手术切除的肌体、内脏为打发时间的方式,他成年的作品以死亡为永恒的主题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最近则是在日本电影节之后重新引发对日文的兴趣而开始读电影旬报。果然“百闻不如一见”,206页的杂志内页,只有13页是广告,而且全部跟电影有关,不是即将上映的电影广告、就是旬报新刊号的内容预告,还有一些电影相关书籍的广告和介绍,其他接近二百页的内容,完全是关于电影的介绍、报道、评论、论文、专栏,还有大幅电影海报送。800的售价虽然比一般的电视和偶像杂志略贵,但比起后者1/3到一半的广告,旬报明显实惠得多了。而且旬报覆盖面也很宽广,从主流商业制作(好像9月下旬号的Hero特集)、genre film(10月上旬号卷首的Sukiyaki Western特集)到小众的独立电影(9月下旬号有青山真治的特集和他新作Sad Holiday的介绍;10月上旬号更加丰富,除了三池崇史之外,我很留意的广木隆一、荻上直子都有专稿介绍新作,堤幸彦和老牌导演森田芳光也有新作介绍,后者的South Bound更加集合天海和丰川悦司两个老戏骨)、还有动画片(9月上旬号封面是Evagelion最近剧场版)和洋画(十月上旬号有Spiderman三部总结和La Vie en Rose的专稿)。有传统和声誉的杂志始终会努力live up its own name。

原来旬报也有两三篇视评,而且每篇都是整版的,既从专业角度讲制作,也同时观测业界生态。好像新鲜出炉的10月上旬号(本来应该是10月1日发行的,不懂为什么我朋友9月22日就帮我在银座买到)就有朝日黑泽明SP《天国与地狱》的点评,文中肯定导演鹤桥康夫在location hunt上面对原著的成功改编、在surveiliance scene混合camera work跟声效在小屏幕创造mise-en-scene的功力,还有通过吹石一惠的角色讲述人生的阴晴圆缺是这部SP相较于原著最有originality的部分。但文中也指出这部戏的硬伤也很明显,主要在角色设定上。好像妻夫木的冷血罪犯形容自己置身地狱的自白缺乏说服力,特别是跟他在04年同样跟朝日合作的SP野沢尚的砦なき者里面玩弄媒体的冷面罪犯(低温犯罪者)相比更显薄弱(砦なき者网站:
不过可惜,这里的书店每年入荷的旬报非常有限,今年只进了两期,都是因为J家做封面人物才得以引入(4月岚的《黄色眼泪》和9月下旬号木村领衔的《Hero》),其他时间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这次比较幸运正好有友人去日本开会可以帮我买,但总不会每个月都有朋友过去吧。![]() 所以在此也想向erica和其他朋友求助,怎样在海外可以订阅日本的电影旬报。
所以在此也想向erica和其他朋友求助,怎样在海外可以订阅日本的电影旬报。